1978年,有这样两幅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中国画”:早春二月和仲秋九月,一群群农民工人军人中学生,肩上背被褥行李,一手提着装脸盆饭盒的网兜、一手举着入学通知书,站在各大学的新生报到处,画面中的他们有三十五六岁的农民,也有十五六岁的中学生,相去万里的形象气质里透着同样的神情,那是做梦都没敢想象的理想来访时的笑面如花,那是与美好未来握手的慌张或张狂——这春秋两画面中的人群分别被历史定名为77级和78级。
何其有幸,改革开放大潮起,我们踏浪而行45年,画中的少年青年已是中年老年,77、78两级也基本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家国责任,于是,我们有时间回望,转头间,我们很多同学望见的最清晰、最动人的景致就是“我的大学”。
好吧,让我们把转头间那深情的回望纪录下来,倾诉给同学们听,给过去听,给未来听——
山东大学政治经济学系77、78级同学说“我的大学”之(1)马建堂:关于高考和十年求学的回忆......
1958年农历四月,我出生在山东省滨州市的农村,当时叫惠民地区滨县彭李乡马家村。这是鲁北平原、黄河岸边、邻海不靠海、土里刨食吃的一个普通村庄。到我出生时,这里早已旱涝灾害频繁、土地盐碱化严重,是有名的鲁北穷壤。我家历代务农,家境贫寒。爷爷马桂林曾任村农会主任,为人正直,因患胃癌,六十岁出头便去世了。父亲马松田,上过高小,是我们家第一位“知识分子”。他早年务农,曾在20世纪60年代初当过村会计,后来被招工到滨县油棉厂工作,退休前是滨州市生资站科级干部。
也许是祖辈深受文盲之苦的影响吧,我从小对书本有种天生的痴恋。那个时候我的家乡是文化的沙漠,家境穷苦,也没钱买书,但凡是有字的东西我都会找来看,然后如饥似渴地阅读。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的《新建设》杂志,还是我姑父南云亮从山东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带回来的篮球教材,我都看过,尽管里面的内容大部分不懂。一本残缺不全的《水浒传》,我熟得都能背诵章回题目了。由于从小学习成绩好,1972年初,我和村里其他4名同学一起被推荐到北镇中学高中部学习。名字听起来虽极为普通,但北镇中学是整个惠民地区最好的中学,由于惠民地区的地委和行署坐落在北镇,所以这所全地区最好的中学叫了这个不起眼的名字。当时的北中名师荟萃,学生也大多都是地区干部子弟。来到这所名校学习,我好似久旱逢甘露的幼苗,不断吸吮着知识的甘泉。特别是教语文的李海鹏老师对我青睐有加。当时我写了一篇名为《管得严》的叙事性作文,李老师批语说,“你在这方面有些天赋,望好好努力。”李老师的批语对一个十几岁少年的激励是如此之大,1978年高考我第一志愿报考的就是山东大学中文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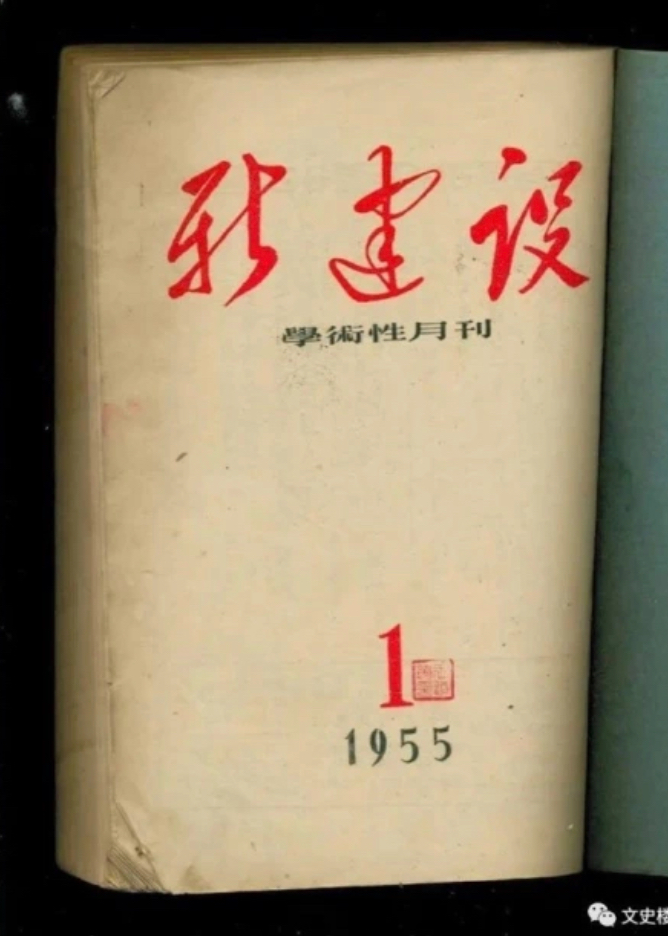
按照当时的学制,我应在1973年底高中毕业,但1973年国家决定恢复高中三年学制,我高中毕业时间变为1974年底。但刚进入1974年,由于“张铁生高考白卷”事件,全国上下开始批判教育战线的回潮,我的高中学习生涯在1974年4月份就草草结束了。由于高考制度当时已停止,我只好回到马家村,当上了村办工厂的翻砂工,从小编织的文学梦、写作梦几乎破灭。然而苍天有眼,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并于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我同百万同龄人样,又看到了希望,我开始在劳动之余准备高考。1977年的高考是在12月10—13日,整个备考的时间是在冬季。那时农村家里无暖气,我住的东屋也没炉子,滴水成冰、寒冷难耐。我披着厚厚的被子、点着煤油灯艰苦地复习。一晚上下来,手是凉的,鼻子是黑的。幸而高考过程还算顺利,我通过了初选,加了体检,报的是莱阳农学院和马鞍山钢铁学院,但不知何故,最终没有被录取。

滨县像我这样通过了初选但没有被录取的考生有20多名。滨县教育局先把我们分到各个乡镇联中,担任代课老师。其间我曾给初中生上过两次课:第一次讲清明节有感,讲介子推背母自焚绵山,讲1976年北京“四五”纪念周总理,这次上课比较成功;第二次讲鲁迅先生的《记念刘和珍君》,这次讲课效果不好,听我试讲的张老师在台下直皱眉头。没过几个月,县教育局就把我们20多个人集中到滨城教育局集中复习,准备高考。这次复习备考就没有上次那样辛苦,一是脱产复习,教育局还发20多元的“薪水”;二是季节好,是在春末夏初,不冷不热。经过1977年的历练,1978年我考得更好,考试成绩是353分,好像是全县第二名。填报高考志愿时,第一志愿是山东大学中文系,这里有冯沅君、陆侃如,有肖涤非、高兰,是醉心文学的青年心驰神往的地方。然而,不知是语文成绩不高,还是其他的缘故,我接到的是山东大学经济系的录取通知书。
1978年9月6日,我坐着滨县到济南的长途汽车,告别了养育自己20年整的鲁北故乡,来到“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省会济南,开始了我面壁十年、苦读生涯的第一站。

山东大学是一座具有光荣传统的著名学府。她的前身是私立青岛大学和华东军政大学,1958年由青岛迁到济南。由于数度磨难,20世纪70年代末的山东大学虽不像20世纪50年代初的5院18系那样鼎盛,但也是国内闻名的重点大学。浩如烟海的藏书、诲人不倦的师长和崇尚治学的校风,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我在母校宽阔的怀抱里尽情地吸吮着知识的乳汁——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到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还有黑格尔的《小逻辑》、锡克的《第三条道路》和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国》……我的十年求学经历,数大学四年最为艰苦和紧张。1000多个日日夜夜,几乎全是由宿舍-教室-饭堂三点一线组成的。每天的学习时间高达10小时,每周平均约60小时。学校每周六的露天电影几乎是我唯一的消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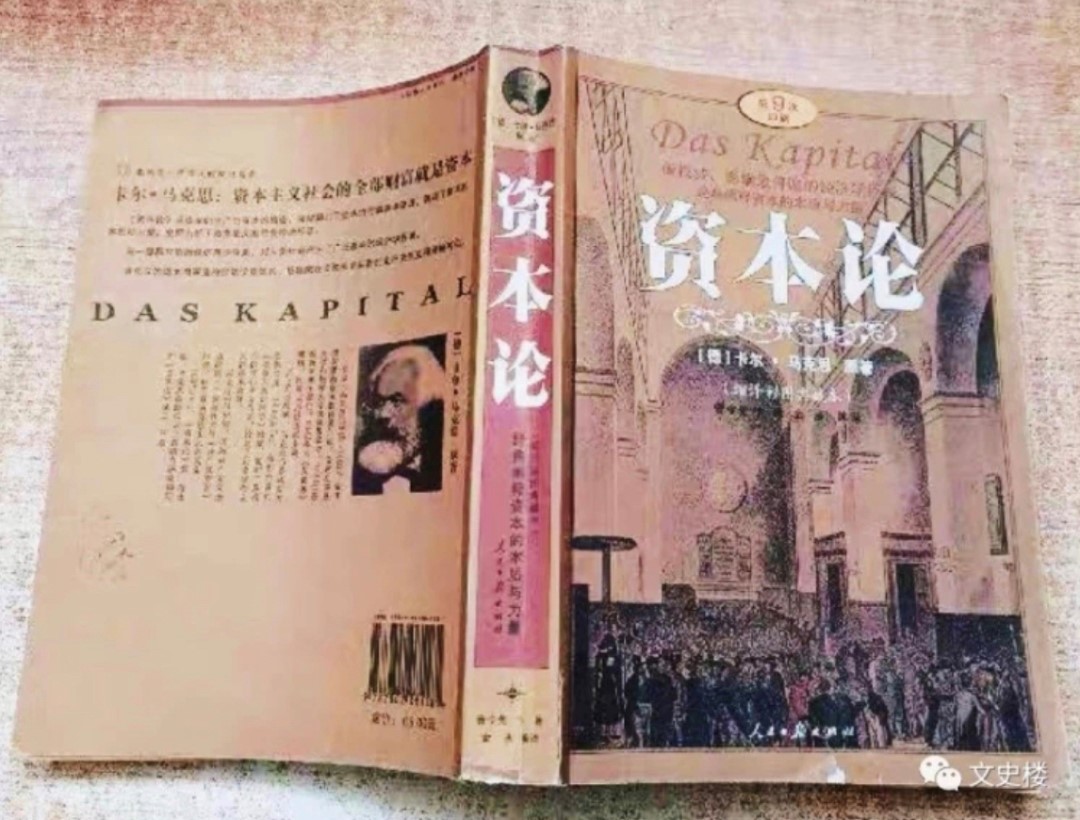

上大学期间,我写了很多的读书笔记。大多不是写在书本上,也不是写在信纸上,而是写在放假从家带回学校的草纸和废旧账页的背面。不只是学习紧张,要发奋补上失去的岁月,我还舍不得吃饱肚子。我家兄妹四人,我是老大。读大学期间,二弟在济南当兵,三妹与小弟仍在上学,家中承包地全靠母亲一人照料,父亲在生资站工作之余还要搬运装卸挣钱填补家用。我本来是家中的“壮劳力”,现在却成了“不劳而获”的纯消费者。一想到父母的辛劳,我的心中愧疚万分,唯一能报答的,除了好好学习外,就是节省节俭,让父母少贴补一点。我父亲是1998年去世的,他在这个世界上只待了63年,每当我想起父亲年过半百仍扛包装运的身影,便泪如雨下,不能自已。
上大学期间,国家的改革开放大幕刚刚拉开。农村改革的重心是推进承包制,继思想理论战线上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后,经济学界开始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什么,以便为重视消费重视分配寻求理论依据。我第一篇“发表”的文章,是1981年暑期回家调研承包制而写的,刊登在1978级经济系自办的油印小报上。可惜在写作本书时,没有找到这篇文章。1981年山东大学举办“五四”学生科学讨论会,我撰写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及实现》论文,获二等奖,奖金50元,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学术活动获奖。利用奖金,我买了同学穿不上的一双二手皮鞋和一件线衣。这篇论文指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保证劳动群众生活不断提高和全面发展的消费资料和自由时间。要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就需要按照社会的消费需求结构建立相应的劳动结构、生产结构、分配结构和市场结构。这篇文章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我日后研究经济结构问题的前奏,也是我在学习期间参与国家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讨论的开始。在文章中,我把保证劳动者全面发展的自由时间也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一观点还是有点青年人的创造精神的。发奋读书、关心国事这些特质,在1977级和1978级大学生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是因为我们险些失去了进大学的机会,才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生活;也是因为我们的命运与时代、与国家息息相关,改革给了我们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们才格外自觉地参与改革开放的讨论。我有一个英年早逝的大学同学,在学习期间还曾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呈送了8万字的改革长文。
1982年9月,我以优异成绩考入我国声誉最为卓著的经济研究机构之一——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攻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向的硕士学位,导师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教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成立于1929年,是我国最早由大学创办的经济研究机构。国内外许多知名的经济学教授,如何廉、方显庭、刘国光、滕维藻、杨叔进、谷书堂等都曾在该所工作或学习过。在谷书堂教授的指导下,我一方面继续吸收、消化着各家经济学的精华,一方面锻炼、提高着我的科研能力。谷教授为了培养我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功,防止因急于求成而带来的学根不深、学风不实的毛病,给我制订了一个三阶段循序渐进的培养计划:第一阶段,主要学好各门研究生课程,掌握各种必要的科研手段,为日后的科研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阶段,结合各类经济学专题,在大量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写出相应的讨论综述和评论;第三阶段,撰写硕士论文。这一培养方案使我受益匪浅。

在南开大学求学时期,适逢党的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在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胡耀邦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要在深化农村改革的基础上,对主要分布在城市的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实行经营管理上的责任制,并有步骤地改革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办法,改革劳动制度和工资制度,建立起符合我国情况的经济管理体制。在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会号召,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全会明确,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着力确立国家和企业、职工和企业的正确关系,并对国家的计划管理体制、价格体系、劳动分配等进行相应的改革。我在南开大学求学时期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就是在这一改革大背景下进行的,主要集中在劳动工资和计划管理体制这两个紧密相连的领域。
我是从1984年开始在国内报纸杂志上正式发表学术论文的。第一篇文章是《也谈我国现阶段个人消费品分配方式——与王勤同志商榷》,发表在1984年第2期的《经济问题》杂志上。据不完全统计,我在1984年共发表12篇论文,其中7篇是研究工资制度改革的;在1985年共发表15篇论文,其中4篇是研究工资制度改革的。我之所以在1984年前后集中力量研究按劳分配和工资制度改革,与上文所讲的“我国经济改革重点转移到城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搞活国有企业”有直接关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围绕这个中心环节,主要应该解决好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即确立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确立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
如果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把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是我研究劳动工资问题的大环境的话,那么我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专业定位则是从事这一研究的内在逻辑。当时南开大学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专业研究生的培养,重点学习内容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的硕士生导师谷书堂教授也集中研究劳动价值理论和按劳分配理论,他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重含义与价值决定的关系问题,在政治经济学界引起了比较热烈的讨论。学习劳动价值论,很容易地就会和当时的改革实际联系起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从自己的专业和老师的研究领域出发,用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来分析国有企业内部工资改革的必要性,并提出“国有企业要贯彻按劳分配理论、体现多劳多得,就必须破除分配上的‘大锅饭’,实行浮动工资”这样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我和徐振方老师合写的《试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突破口》(《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1984年第3期),以及发表在1985年第5期的《东岳论丛》上的《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与浮动工资》。
这一时期我的第二个主要研究领域是计划管理体制改革。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生产由国家计划指定、产品分配由国家调拨、工资总额由计划确定。随着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改革必然触及国家对经济活动、对企业生产流通和分配方式的调整。在谷老师的指导下,我的硕士论文研究方向选择了国家计划管理中的“条块”关系这一研究领域。所谓“条条”管理,是指由中央部委直接管理国有企业,“块块”管理是指由地方政府直接管理国有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大型的国有工商企业一会下放,一会上收,在“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再收”的怪圈中徘徊,而没有解决国有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相对独立经营实体这根本问题。
我的硕士论文《论国家直接管理方式的转换》,分析了传统“条块”管理模式的弊端,提出计划管理体制改革,一要确立国有企业的相对独立地位;二要改变传统的指令性计划管理模式,国家对企业的管理要从直接控制型向间接调控型转变。这些观点和两年后党的十三大所提出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思路是一致的。我的硕士论文后来被收进经济日报社出版的《经济学硕士博士论文选(1985)》。论文答辩后,我经过修改和继续研究,在这一领域陆续发表了10余篇论文,主要有《新型计划体制的目标模式及其理论依据》(与谷书堂合著,《南开经济研究》1985年第5期),《试论我国部门管理方式的转换》(《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6年第3期),《改革宏观管理体制破除条块分割》(《南开经济研究》1986年第1期)等。
在南开大学学习期间,改革大潮风起云涌,经济学界百家争鸣,当时的青年学子更是英姿勃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因天津靠近北京之地理优势,南开大学学术氛围浓厚,一时也是藏龙卧虎风云际会,杜厦、李罗力、金岩石、常修泽皆是当时青年才俊。1985年4月,我有幸参加了“第二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与浮动工资》文章从2615篇论文中脱颖而出,成为125篇会议入选论文之一并获奖。这次会议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宣部理论局、红旗杂志社、经济日报社联合举办的,会议层次很高。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薛暮桥热情洋溢地题词:“济济英才,满腹经纶,青出于蓝,后继有人。”确如薛老所言,参会人员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改革开放后活跃于政界和理论界的人士都可以在与会者中找到他们的名字,如马凯、马飚、郭树清、楼继伟、李佥阁、徐景安、华生、周其仁、张维迎等。当年5月,我也凭借研究劳动工资问题的论文参加了“天津中青年学术讨论会”,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张再旺同志专门给会议题词“中青共聚,新老合作;同心同德,献计献策”。
1985年7月,我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毕业,并留在这里工作。不久后,经过认真权衡,我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孙尚清研究员的1985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结构。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5年秋季要从京西的十一学校搬至机场路酒仙桥,故我们1985级博士生是在1986年2月份报到的。

与一般的大学相比,中国社会科学院(简称“社科院”)研究生院是一所比较特殊的学校。研究生们的人事关系在研究生院,学术关系却在各个研究所,而学生的培养又主要靠导师“私相授受”。所以有人曾戏称研究生院为一个“学生公寓”,这里绝无任何不敬的成分。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其他大学不能比拟的优势。中国社会科学院汇集了全国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大家巨擘,从广义上讲,他们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生们的老师。研究生院本身又吸纳了社会科学各个“行业”的青年俊秀。他们不少人在社会上已有很高的知名度,如文学系的刘东、许明,哲学系的何光沪等。比我们高一级的还有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郭树清、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王逸舟文学所的王友琴,当时也都是人中翘楚,不少人现在已成为各自领域的大师、泰斗。在这种貌似松散、实则优秀的环境里,在这些后起之秀的“侃谈”中,不知进发出多少闪光的火花,而这些火花又汇聚成夺目的火龙,照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牌匾。
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的三年是我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是学术论文、著作产量最高的时期,1986-1988年三年间我共发表论文59篇。我一生引以为傲的博士论文《周期波动与结构变动》自然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与孙尚清老师合作研究产业结构的专著也是这一时期写就的,我本人最满意、在学界影响最大的论文《企业行为与经济机制》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知名国际经济学教科书《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是这时期译毕的,言辞锋利、销量可观的《偏斜的金字塔》《走出迷宫》(与宋光茂合著)也是这一时期写作的,同时我还发表了不少时评、书评和言论。回首这一时期的学术生涯,我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企业行为和产业结构这两个领域。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对企业行为的研究,是我在南开求学时期研究劳动工资问题的深化和继续,有些观点也是在南开大学学习期间形成的。我观察到,随着国有企业分配自主权的扩大,国有企业工资分配虽然初步解决了计划分配体制下统得过死的分配平均主义的弊端,但国有企业所有权的虚置与分配权的扩大又带来了另外的问题:消费基金膨胀和经营者对所有者权益的侵蚀。这促使我进一步研究企业分配行为“死”与“乱”局面的深层原因,探究企业行为层面的内在深层机理。围绕这一领域,我从1985年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企业行为的改变与工资的宏观控制》(《经济研究》1985年第6期),《企业行为与经济机制——兼谈作为企业行为合理化条件的国家所有制的改革》(《经济研究》1986年第2期),《体制转换时期的企业行为》(《中青年经济论坛》1986年第1期),《所有制与企业行为-再谈所有制改革》(《企业界》1986年第11期)。
这些论文比较早地把国家所有制改革与企业行为合理化结合起来,比较早地探讨企业行为层面的深层机制,实际上还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也正是因为我在这一领域的开创性贡献,《经济研究》这一经济学领域名列第一的刊物连续刊载了我的两篇论文,并将我列为有前途的青年经济学家,我也真正开始在全国有了些学术影响,有些观点被多次引用。有位研究企业行为的学者曾大段引用我的观点而不具名,事后我们认识后还专门向我道歉。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联合《经济研究》编辑部,在杭州召开了“经济机制研讨会”,我以《企业行为与经济机制》一文入选参会。这篇文章以醒目位置发表在翌年《经济研究》第2期上,《经济研究》编辑部还推荐这篇文章角逐第三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
产业结构是我攻读博土学位的研究方向。1986年2月,我正式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到入学,在继续深入研究企业行为的同时,也开始将研究重点转向产业结构研究。
最初我的研究重点是第三产业。传统经济理论不认可三次产业划分,不把第三产业作为创造价值的产业对待,在工作指导上,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服务业“欠账”太多,供给严重不足。尤其是随着几千万下乡知青返城,城市吃饭难、做衣难、住店难,行行皆难;出行堵、乘车堵、购物堵,业业都堵:“开门七件事,事事跑断腿,样样排长队。”面对这样的局面,我开始研究第三产业问题,尤其是第三产业严重滞后的原因,我认为政府投资和价值补偿双重不足是第三产业滞后的主要原因,生产、生活服务业的非产业化、非社会化扭曲了第三产业的供求格局,传统计划体制的弊端以及由此制定的政策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1986年下半年到1987年上半年,我先后发表了5篇研究第三产业的文章。
1987年,根据孙尚清老师的安排,我着手撰写《中国产业结构研究》专著。这本专著是作为第六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六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研究丛书》的其中一本,丛书的主编是马洪、孙尚清。在孙老师的指导下,我系统地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产业结构演变历史,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演化规律的动因,对产业结构进行了国际比较,指出了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六大问题,提出了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合理化的建议,并对我国产业结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这也是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2012年,我和江小娟、周叔莲同志一起荣获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这部著作的学术贡献是一重要原因。在撰写《中国产业结构研究》时,我发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伴随着两种变动,一是周期性波动,二是结构性变动。二者关系有无规律可循?二者相互关系的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成为我博士论文研究的主题——周期波动与结构变动。在研究领域和题目确定后,我便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地开始工作。首先是到国家图书馆、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广泛搜集主要国家经济周期的各个产业、行业的产值,就业人员的历史统计资料,时间序列跨度百年之久。其次是阅读大量文献,并做笔记和卡片。当时做研究,计算机还未普及,不像现在这样方便,需要自己做卡片,分门记载,分类手记。然后是深入思考、整理思路,形成自己的观点。有时晚上入睡时,突然形成了某种观点或想法,或者对一些难题突然有了灵感和感悟,便马上起床,将其记录下来。最后是攻关冲刺,撰写论文。当时我在研究生院宿舍门上写了“论文写作,谢绝打扰”八个大字,连续奋战了30个日日夜夜,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
《周期波动与结构变动》主要研究内容有三:一是不同类型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经济结构变动规律;二是周期波动影响结构变动的机理;三是我国周期波动中结构变动的共性和个性。承蒙湖南教育出版社帮助,在1990年将其出版。首次出版近30年后,在我的学生覃毅同志联系下,商务印书馆将其再版。
我在博士论文中使用了大量发达国家的历史统计资料,在博士论文准备和写作中,深感经济研究中统计资料的重要性。20年后,中央任命我为国家统计局局长,我在这个重要工作岗位上服务了6年半,让自己能为中国统计事业做一些实事。我的10年学术生涯,独著、合著20余部,如果要问我对哪一部最满意,哪一部学术价值最高,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周期波动与结构变动》,尽管它没有直接获奖。在研究写作博士论文上的付出和收获,我深深感到博士期间学习时光的珍贵,深深感到博士论文的神圣。正是基于这些经历、感悟和认识,我对我门下博士研究生的论文指导都特别用心,要求也非常严格。如果我的学生们能读到这段文字,也许更能体谅老师严格要求的苦心和责任感。

转自文史楼公众号